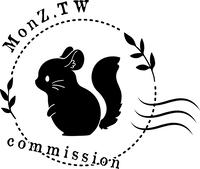【樹根下的夢】
前輩→白王
微虐注意
微虐注意
|
那是在被冠名為新一任的空洞騎士、聖巢之王、深淵之主的小小鬼魂,透過外來者的意識凝聚,從夢之世界中將瘟疫之光扯碎後很久很久的事了。 被根除的瘟疫消失後,身為失敗品的它也隨之從封印裡解放,數百年為曾落地的身軀脆弱而失衡,曾經的王國第一騎士只得用骨釘撐起身姿,踉蹌的步伐甚至將看守在神殿門口的、它名義上的妹妹嚇得舉起骨釘。 在一陣慌亂中它被大黃蜂帶往附近的小鎮進行包紮,在她的碎念聲中理解了現世的全貌。 聖巢已經衰敗,哪怕瘟疫被驅散,也回不到從前繁榮的光景。 蒼白之王的餘輝依舊守護著聖巢,但他的本尊卻已不知去向,失去了神王的領導,無助的蟲民們最終只能走向潰散。 稍事休養後,大黃蜂帶著它走過了很多地方。 跟他有關的地方。 它見到曾是華美宮殿的遺址,貧瘠而荒涼, 它見到深淵大門前悔恨且自責的碑文,心頭一陣泛酸, 它見到了作繭自縛的王后,在無聲的回應中接受了她的懺悔, 它見到了淚之城的雕像,有那麼一瞬間,覺得被記念、歌頌在此的,並不是它。 不該是它。 它是失敗的容器,它沒有成功封印瘟疫。 它是白王精心設計、拯救聖巢的計劃中唯一的敗筆。 它把自己藏的太好,導致最終的滅亡。 是它帶來了聖巢的毀滅。 它不該被歌頌、被記念、被蒼白的王與王后扎在心中,訴說著無盡的懺悔。 然而就算它渴求著王的苛責、王的嚴懲,那曾經的神王也已經不在了。 它空洞漠然的表象底下深愛的父王,已經不在了。 它沉默的跟在大黃蜂身後邁開步伐,繼續進行著聖巢的巡迴之旅,帶著即將送葬這一切的心情。 最終它們在王后花園分離,容器選擇了有著巨大白王雕像的遺址作為落腳處,搭建了簡易的小屋,帶著對王的回憶與一份守護王后的心思,在這綠意盎然的一處隱居了起來。 也許從那天起已經過了很久很久,深居於此的容器沒感受到太多關於時間的概念,它們也幾乎不會衰老,所以它只是日復一日的活著。 本就細心的容器學會用骨釘修剪過於茂盛的枝芽、用盛開的花朵裝飾白王的雕像,偶爾去王后的門前,替昔日的戰友與王后獻上一束花。 容器的生活平淡而樸實,所以當它查覺的時候,那個東西已經長得有模有樣了。 那是一個新生的低語之根,就長在容器照料的花圃一角。 傳說低語之根是思念的凝聚,靠吸取土地的歷史與記憶成長。 雖然它不太明白在這幾乎只有他一個蟲子生活的地方怎麼會孕育出新的低語之根,但他也欣然接受了這個稚嫩且無害的枝芽加入他的生活。 只是不管昔日或現今都深居簡出的容器,並不曉得關於低語之根的另一個傳說: 『在樹根下睡著,會作生動的夢。』 某日,當陽光照射在花園的樹頂,被葉子揉碎成無害的光線後灑落在花圃的草坪時,過份祥和的氛圍讓容器也產生了一絲睡意。 『就這樣順著自然,稍為休息一下也無妨吧。』它想。 於是它依靠著低語之根、在微風的吹拂中漸漸進入夢鄉。 當容器回過神來的時候,它發現自己正身處於黑暗之中。 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虛空蔓延至視覺盡頭,突如其來的狀況與過份的寂靜激起了它作為一名戰士的防備。 容器環顧了一下自身,愛用的骨釘此時並不在它身邊。 正當它打算移動的時候,一陣刺眼的白光從它眼前炸裂,它屈起身子擺出戒備的姿態,用僅存的獨臂遮掩光線。 正當容器瞇起眼睛,令視覺稍稍能夠適應後,映入眼瞳的畫面卻讓它的思緒宛如凍結。 蒼白的外殼、嬌小的身軀,薄透的羽翼上有著七彩的折射。 那是它以為此生再也見不到的人物。 它的父王。 轉眼之間,周遭的一切已轉變為它記憶裡的白宮,而它自己就跟蒼白之王佇立於他倆再熟悉不過的長廊上。 然而容器沒有多餘的心思去分神細想,他的目光緊緊的落在白王身上,生怕一個眨眼就再次失去他。 「騎士?」 白王的嗓音喚回了容器的思緒,它凝視得太過專注,甚至忘了對王行禮。 它慌忙的單膝跪了下來,雖然情緒上還在震撼之中,但它的身體還記得過去的一切,它的動作優雅、行雲流水。 失去了右臂的它不得不用左手行禮,為此的愧疚感讓它將自己的頭壓得比以往更低一些。 容器無法理解為什麼已經消逝的王會再次出現在它面前,它只知道白王是古神的轉化、是足以傲視眾神的神王。 也許祂又經歷了一次重生,也許祂此刻前來就是為了給自己的奇恥大辱劃下句點,給予它、為這聖巢引來滅亡的可恨廢品帶來它期盼已久的處決。 它低著頭,感覺到蒼白的王舉起了手,然而最終,它企盼的裁決卻未曾落下。 白王纖細的手腕此時正停落在它前方,掌心向上。 那是過去白王從未對它擺出的手勢,一個無聲的邀請。 它的思緒在震驚與不安之中徘徊,視線漸漸凝結,從王的手臂緩緩往上攀升,直到它近乎無禮的直視蒼白之王的容顏。 那依舊是它未曾見過的神態,它記憶中的王總是嚴肅而莊重,心繫聖巢與瘟疫令祂總是眉頭深鎖。 而如今在容器面前的王是它未曾見過、也無法想像的…慈愛。 如同有著無盡耐心的父親,蒼白之王只是靜靜的維持同樣的姿勢,等待手足無措的孩子作出回應。 它最終仍是鼓起了勇氣,顫抖的將自己的手覆上那細白的掌心,並且感受到王的手指收攏回握,將容器的手輕輕握緊 ——雖然他倆的體型相差得太多,蒼白之王只能握住它的兩根指頭。 指尖傳回的觸感溫暖且柔軟,它卻覺得自己的虛空外殼幾乎要融化在這細膩的觸覺之中。 而白王握著容器的指頭,有些依戀的摩娑了幾下後,便引導容器把手搭在自己的腰背上,而祂自己則再次舉起了雙手,讓容器把頭殼靠在祂頸肩。 祂一邊輕撫著容器的犄角,一邊輕拍它的背,它甚至感覺到王的臉側在自己身上輕輕的磨蹭著。 與白王未曾有過的親暱讓容器覺得慌亂又無所適從,它不敢出聲、甚至不敢作出半點動作,生怕有任何差錯就失去這奇蹟般的時刻。 而最後打破這寂靜的仍然是白王的嗓音。 它聽見王的聲音在耳邊迴響,它感受到王輕撫著它的背脊,柔聲的說著對不起。 它想搖頭、它想回應,然而它的身軀依舊一動也不動。 接著它聽見王細數著他們一起度過的每一段時光,讚美它的成長、感謝它的付出,惋惜它的傷痕。 當它聽見白王稱呼它為孩子,並且訴說著它作得已經夠多了,要它別再為這一切自責的時候,它終究是忍不住收緊了手臂。 ——湧到嘴邊的一聲『父王』還來不及說出口,下一秒它便發現自己從低語之根的樹下驚醒。 王的雕像立在後方,面具鳥從空中飛過,引起一陣微風。 綠色的樹葉灑落,王后花園依舊沉靜。 而它最終學會放聲哭泣。 Fin. |